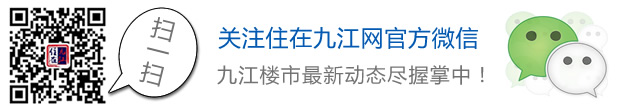从本届政府的任期以及经济运行周期来看,今后两年应是一个于地方于开发商于政府于买房人的一个特殊时期,而特殊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房价出现结构性波动,但鉴于政策,并不会出现结构性上涨,而结构性下跌则在部分城市是存在较大可能的。
本文旨在通过结构性涨跌的判断来理清楚买房基本原则。
结构这个词席卷三十年来的中国画卷。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经济中心议题均离不开结构,八十年代的价格结构调整或者说价格改革,九十年代的结构性通胀,本世纪初的结构转换,包括现在的收入结构政策性调整。
因此,有人巧妙地将结构性涨跌引入到对房价的分析与预测,在新政及各地公布房价控制年度目标后,观测市场并得出结论是部分城市出现结构性上涨,部分城市出现结构性下跌。
事实上,在目前的政策面前,谈不上结构性上涨,但有可能结构性下跌。
为什么不存在结构性上涨呢?
因为更广泛的三四线城市事实上不存在房价下跌,而在这些地方政府眼中也根本就不认为房价过高或高,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地出台了房价控制目标,最为显著的内容是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实施目标,对与调控相关的内容也仅限于闲置土地及公开本地购房的首付比及信贷要求。而房价控制目标更多与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而我们知道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统计本身就是个谜。
既然无上涨,自然谈不上结构性上涨,接着就是一二线城市,是否会发生结构性上涨?
有媒体举例说明,广州出现结构性上涨,即房价上涨而成交量下跌,并判断是因为成交部分系中高档住宅,或者价值洼地的供应,而诸如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则根本没有出现价格上涨的情形。
真正的结构性上涨是与成交量及成交单价挂钩的结果,不外两种情形,即中高档住宅价格高并成交比例超过了中低端住宅的成交量从而让统计结果出现价格上涨的情况。
事实上,支持中高档住宅成交的理由并不充分,限购及停止三套房贷已经足以消灭大部分的投资投机消费。
那么,为什么结构性下跌却存在可能或者说是必然的呢?
务虚地说,从全国范围内房价存在有升有降,在一个区域不同城市出现价格的涨跌互现都属目前的正常现象。只要一个城市依赖投资投机消费把价格涨起来,这个城市就必然会因为政策原因出现价格的波动。
结构性下跌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是开发商的实力不平均,因此一些资金链紧张或者只有一两个项目的小开发商,在目前的政策预期肯定不敢硬抗,因此选择降价销售,只有那些大型开发商或者资金来源充足渠道畅通的才有可能通过暂缓开发速度来对抗政策以谋求未来发展机会,更有可能调整不同城市的开发进度来平衡销售。
其二是地价层次决定率先降价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因为多数城市的住房供应与土地供应时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那些早期获得的土地形成的住宅供应具备降价空间而后来者即高房价支持下的土地形成的住宅供应则不太具备降价空间,而具备地价优势及规模优势的项目,在目前政策态势下既有降价空间,又有相当降价效益,因此可能象万科零八年那样的选择率先降价。
其三是过去的2009/2010两年已经消除了结构性供求矛盾,如果说有什么矛盾,也仅仅是多数城市旧事重提的要求新增供应必须贯彻90/70政策,而在过去两年完全消除存量,保留的房源都是开发商有心栽花的结果。在此情形下,目前支持市场成交的刚需及部分改善需求,均与市场供应结构是同步的,如果说不同步的情形,一定是房地产发展畸形的城市,即过于依赖投资投机消费的城市,象威海代表的滨海投资区域、象北京代表的移民投资区域、象上海代表的产业集中区域、象海南代表的泡沫集中区域、象深圳代表的空心化集中区域。
充分认识市场的这种特点,既有利于开发商阵营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动调整价格策略,一线主动降价,二线谋求性价比销售,三四线城市有保质前提下保量;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合理制订本地城市化步伐;还有利于决策层认识市场的本质变化,制订有利于楼市平衡发展与房价保持合理水平的针对性政策。
对于买房人而言,认识这个特点有利做出合理决策,处于一线的暂缓买房,处于二线的,只要不是笔者提及的供求不同步的五大类区域,则可以量力而行;处于三四线城市的则越早买越好。